|
我和儿子是校友,汶河小学的校友。
同一个母校,两代人的时空,母校因此有了巨大的变化。
在这巨大的时空中,我们也呼应着母校的变化而变化。我吮吸着母校的滋养,长大了,长高了,如今我的外孙也快有了读小学的年龄。如果不是在海外,我还是让她读母校。我的儿子也长高了,长大了,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,有了一个他自己奋斗的目标和打拼的天地。
俗话说,吃水不忘开井人,追溯如今的这一切,应该是母校源远流长的那一端。每每想到这里,我就感恩我的母校,感恩我的老师,感恩母校赋予我们的香甜至今、流淌在血液中的滋养。
我儿时的母校建在毓贤街,一条幽长、光滑的青石板小路,两排古色古香的民宅,阮家祠堂让这条小巷飘逸着深深的古韵。当时的母校十分的简朴,几排教室,一座小楼,一楼是五年级,二楼是毕业班。一、二年级设在分部,三——六年级设在总部,每个年级两个班,满打满算500名师生。但是,凭着实力很不一般的师资,当时的母校却能傍着幽深的古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。
小学六年,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毕业班的的数学老师。老师大姓张,名海深。根据老师的起名,你完全可以断定老师的长辈应是文化人,你瞧名字起的多气派、多韵味,大海的海,深邃的深,像大海一样的深邃。老师果未辜负长辈的哺育和期待。在我的记忆中,老师才华横溢、快人快语,浓眉大眼、英俊潇洒,起码是汶河小学的“栋梁之才”。后来,我还得知,老师是被打成“右派”贬到我们所在的汶河小学来的,再后来还参加过建国后新版《辞海》的编撰。老师的才学大得很呢!在我们嗷嗷待哺之时,能遇到这样的一位好老师,真是三生有幸,快哉!快哉!
在他的教导之下,我们的数学好像都学得不错,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我们那个班似乎不存在现在所谓的“差生”。只要上数学课浑身上下都来精神,什么“追击问题”、“鸡兔同笼” 、“等分问题”等等的数学难题,到了他那里就是小菜一碟,他可以十分详尽、条分缕析地給你一一道来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你想糊涂也难。临毕业时,他将所有数学题,分别归类,理论对试题,试题对理论,真是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楚。不仅如此,而且天天出新、越听越想听,越学越要学,听他的数学课,就像遨游在知识的海洋,刺激、诱人、享受。每天都把我们辅导得很迟很迟,但不收我们一分钱的课时费,纯粹的奉献,放在现在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后来,初考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好,整个班级的同学一个个都考上了当时的扬中、附中、新华、市一中这样的名校。我呢,当然也没有辜负老师的一番心血,考进了现在大家都羡慕的扬州中学。不过,我有点瘸腿,语文有点差劲。至于后来怎么阴错阳差地选择了文科,那可是“文革”以后值得反思的事了。不管怎么说,尽管我没有多大的出息,但没有让老师失望,没有寒碜我的母校。
再后来,儿子也进了汶河小学。不过,不是classmate,而是schoolmate。儿子读小学的时候,汶河小学迁址到后来的石塔寺附近。校舍有变化,但不大,不如现在的气派和壮阔:立在校门口,越过银灰锃亮的铝合金拉门,整个校容校貌一览无余,四、五个人合抱的银杏树顶天立地、郁郁葱葱,一座三层楼洋溢着现代气派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,被阳光涂抹得明亮、气派,宽敞的操场中央立着三十余米高的旗杆,五星红旗在蓝天下呼啦拉的飘扬,庄严、肃穆、幽静。儿子在八十年代读完六年小学后,也告别母校启航新的人生。
我想儿子和我一样,最难忘的是他的班主任王老师。王老师微胖、富态,笑容可掬,待学生亲如子女,谁有孩子放在她那里一百个放心。
为什么这么说?儿子,从小体质弱,一坐汽车就晕车,直呕吐。所以,每每春暖花香,学校里组织小朋友专车春游瘦西湖、平山堂,儿子去不了就一个人待在家里。这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遗憾。不得以,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,我们举家为他出游瘦西湖、平山堂,不让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什么阴影。不过,不能享受集体的愉悦,还是一个遗憾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,我们也没有很在意。可王老师,却记在心里。在六年级的最后一次春游,王老师破例组织步行春游。很明显,是刻意把儿子带上,为儿子补上这五年些许缺憾的一课。更难忘的是,王老师的儿子,也在队伍之中,我的儿子跑不动时,王老师就用自行车驮着他,而王老师自己的儿子则一路步行。就冲着这件事,我一辈子都感恩汶河小学的王老师。
所以,儿子小学毕业以后,每年我都带着他去看望一次王老师。儿子婚礼时,我还刻意邀请王老师赴宴、致辞。我之所以这样做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感恩。
离开母校已很多年了,我感恩母校,我让儿子也感恩母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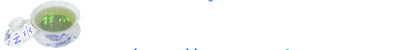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一篇文章: 都是表扬惹的祸
下一篇文章: 《灯下漫笔》教学反思
|